籌委會顧問
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博士後。曾任教於紐約州立大學、耶魯大學、佩斯大學、台灣大學、新竹清華等校,1998年到香港城市大學創立中國文化中心,任中心主任,推展多元互動的中國文化教學。2017-2020年出任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主席,2016年獲頒香港政府榮譽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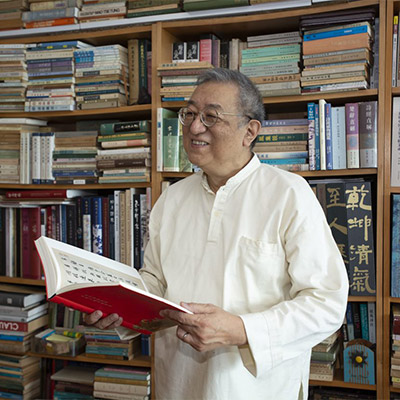

鄭培凱教授在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咨詢委員會工作了六年,剛剛退任下來。這麼多年,鄭教授看到參與非遺的人大部份都是新界的,因為非遺跟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這裡牽涉到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香港人該如何對自己的本土文化作出定位?他覺得參與的政府公務員都很努力,可是社會上的人好像不大清楚非遺的重要性。加上受到社會風氣和歷史背景的影響,一般香港人對於傳統不是特別重視,而真正參與其中的人是很少數的。
鄭教授認為香港有很多特色,除了國際化之外,也有她的「根」,而這是非遺工作中一直希望加以宣傳的。可是因為社會、環境的某些因素,不常聽到一般人或媒體介紹非遺,粵劇是一個例外。有可能因為粵劇跟演藝有關,比較受大家的重視。鄭教授說他最近聽到有一位教授說香港不是中國的城市,是世界的城市,是「above中國」。鄭教授覺得這樣的說法,帶有說話者他個人的嚮往,「在抽象範疇,無所謂對錯。我也希望我不只限於一個地方,而是一個世界人,甚至是一個宇宙人。可是要注意的是,假如有現實的針對性,流於空泛的口號有它實際的危害性。」
歷史性的文化傳統能給人力量,強調一個地方的「根」,不是說永遠都抱殘守缺,而是它會給人一種精神力量,讓人感到生於斯的充實,而這種精神力量在香港很多的非遺中有特殊的展現,這點跟中國内地的不太一樣,反而是跟台灣的比較像。

鄭教授舉了一些例子加以闡述﹕「第一,香港跟傳統宗教有關的東西很多,佛教、道教和民間信仰保存的非常好。内地因為從孫中山開始搞革命,共產黨更是激烈,一整個世紀都以科學為名掃除迷信,文物被破壞掉不少。我記得小時候在台灣讀《孫中山傳》,講到孫中山年輕時就很了不起,跑到佛寺把佛像都打掉了。他的思想進步,可是這種進步的做法跟大多數人的文化心理基礎互相有抵觸。」宗教是一種選擇,不能說民間宗教是迷信,信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就不是迷信。鄭教授記得他去義大利的時候,用一兩個月開車到每個小城去仔細考察,有很多地方保留著聖跡、聖物,「其中有一個是San Francesco的,在Assisi,旁邊還有一個女聖St. Clare,傳說她曾把心剖開拿出一個鉤子,鉤子現在還供奉在那裡,信眾都去朝拜。這是不是迷信呢?」鄭教授相信,有一個信仰是好的,只要不危害道德,不危害別人。香港在信仰這一點上存在意識衝突,但是因為涉及政治因素,無法當作一個比較重要的、整體的社會思維的項目來做硏究,只能從非遺的角度儘量去保護。其實香港人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思考一下,去車公廟祈福、去黃大仙拜神,去看風水、打小人,背後牽涉的東西是甚麼呢?
第二點和中國内地不太一樣的,是宗族性。鄭教授繼續舉例說明,他說﹕「香港宗族的一些傳統習慣保留的蠻好。宗族的東西很傳統,有的是比較束縛人的,有的卻不見得是。宗族最講究的是血緣的關係、親屬的關係、人際的關係,這些在中國文化中都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倫理。從宏觀的角度來看,香港在這兩點上別具特色,背後都牽涉到對於中國文化的重新認識,而且對於人際之間和諧、和平的發展有重要的意義。」


能夠納入非遺項目的一般都有兩三代的傳承,時限是六十年。有的非遺已經傳了幾百、上千年了,比如新界的一些祭祖習俗,是南宋移民承傳下來的。鄭教授指出文化跟人的心理有關,而非遺最重要的是照顧人的心理素質。
在已經列入非遺名錄的項目中,有兩項的爭議性最大,鄭教授深入淺出地講解﹕「一個是鵝頸橋打小人,委員會就此項目多次討論,有的人認為這是風俗習慣,沒有甚麼不好,有的人就提出其中有道德的問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規章裡列明,非遺習俗不能違背善良道德,要往好的方向走,從而提升人的素養。另一個有爭議的項目是觀音借庫,在實際運作當中,牽涉到的問題比較複雜,有點提倡高利貸的意味。如果只是精神上的活動,好像觀音送子,問題就相對的簡單一點。」保護非遺碰到許多類似的爭議,其實是社會的問題,社會問題就需要比較理性地討論。

保護非遺的工作已進行了這麼多年,有一定的績效。非遺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的,是世界性的。中國人在二十世紀意識到「世界性」和「國際性」的重要性,就比較聽從聯合國對保護非遺的倡議。
之前香港政府撥款三億元支持非遺項目,鄭教授記得申請的人數不多。「其中有一些很好的項目,像粵劇承傳的『一桌二椅』、『工尺譜練習』,申請者覺得申請手續太繁瑣, 情願放棄拿資助,這是一個問題。現代社會的政府,按照民主方式運作,有它的複雜性,有時候會讓人望而卻步。非遺諮詢委員會的工作也要面對這些問題,要花很多精神和時間去審核、討論、立章程等。這裡有一些矛盾,也是文明社會發展到後來需要解決的問題。」

鄭教授憶述,效果最典型的例子是「大澳遊涌」。「十年前只有老年人在做,後來被列為香港的非遺,納入國家級非遺,也成為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項目。當地年輕人便覺得很光榮,也很好奇,他們現在都來參加了。因為這能給他們一種自豪感,其實就是一種精神力量,人們都希望被看得起,評為非遺讓他覺得這個『根』是被尊敬的。」
從這點來看,十年來香港非遺多多少少取得了一點成績,鄭教授覺得近年的社會環境不太平靜,所以運作起來還比較緩慢。「推廣文化的、教育的、藝術的人,需要有耐性,一直堅持,時間久了總會有人參與。參與進來的人都會覺得這是好事情,因為它沒有任何壞的方面,不會危害任何人。」


在一個經濟開放的社會裡,有的人覺得,非遺相關的工作報酬太少。雖然傳承是很重要,大家都尊重,鄭教授提及有一部電影紀錄片《戲棚》,拍攝很用心,拍的人也是覺得有使命感,故事道出老一輩搭建粵劇神功戲戲棚的人很焦慮,他們感慨後繼無人,因為工作太辛苦,報酬又微薄,而且相對不穩定,難以以此為生。
「對於非遺傳承人,中國内地一開始每年給他們八千元,現在給一萬元。在以前的時候,這筆錢足夠一些人生活,也能吸引外出打工者回到家鄉恢復祖傳的技藝。所以從整體上,這個辦法在内地是有效的,可是對於香港的經濟環境,這個金額比較沒有吸引力。」鄭教授認為香港的非遺傳承人都很了不起,他們都是有使命感才堅持下來,而不是為了錢。
「内地開始推廣非遺,政府就呼籲,地方上有文化、有傳統就成為一種業績,然後官員就加以鼓勵和推動。好的方面是很多非遺得以保存,避免了消失;另一方面就推出太多項目,比如很多非遺項目,福建有,廣東也有,或者是福建省內每個縣都有,從外面看就有點龐雜。」鄭教授覺得中央可以定一個比較有方向的統籌計劃,讓內行人來參與規劃,將各地非遺項目聯繫起來,方便進行研究。他不建議把非遺跟旅遊結合,因為這樣做就不再是文化遺產了。「譬如說,會有歌舞團的人來教這些少數民族怎麼跳舞比較漂亮。可是人家跳舞是跟宗教祭祀、民間慶典、民族和生命有關,一旦變成了觀光客喜歡看的,就變質了。」鄭教授強調非遺保護力度的把握,需要有識之士的參與。

鄭教授希望有更多的學者參與非遺的工作,他指出現在文科學術界一般是按照理工科、社會科學的方式寫論文,讓這些人去做非遺就很辛苦,因為要做實地的田野調查,需要懂得地方的方言、小調、習俗等等,有點像人類學,可是跟傳統人類學討論的範疇又不同,在學術評鑒上很吃虧,所以造成目前對非遺的研究還是不足夠。
鄭教授一直在探索崑曲的藝術傳承,他發現當中還有更多複雜的研究是值得做的。「非物質文化傳承裡,『口傳心授』有一套的道理,它經常能確保傳承下來的大體模樣不失。做這類研究需要去對比實際存在的東西,比如懂音樂、懂身段的人就能夠追源溯本,這需要許多人的合作。誠然,這對於人文的認識是很重要而且缺失很大的一環。做文史研究的人,最簡單的寫論文方式就是按照文獻來寫,因為理據清楚,可是一些還活著的、重要的東西慢慢消失掉,我們不能放任地讓它自然消失。人類文明從來就不是一個順其自然的東西,非遺保護跟文明的傳承有關,所以份外寶貴。」

日本、韓國和歐洲國家做的非遺項目都比較好,因為他們有很強的民俗認同感,對傳統感覺很自豪。義大利的奔牛節在旁人看是瘋狂,西班牙人也有鬥牛,雖然比較殘忍,鬥牛士可能被牛角刺死,但是他們覺得這是傳統,很光榮。鄭教授再加以解釋為甚麼日本人對於非遺和整個文化傳統這麼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覺得自己被美國佔領了,MacArthur是美國天皇,戰後的憲法是美軍定的,一方面有其現代性的東西,可是另外一方面也讓日本人很害怕,覺得要亡國亡文化了。所以日本就對非遺特別的重視,它可以讓日本文化精神得以延續。」在「文革」以後,中國八零年代也出現文化熱,是一個反彈。因為中國的革命持續了很久,從辛亥革命開始,「五四」打倒孔家店,再一直搞繼續革命,到「文革」, 是一個長期而深化的文化鬥爭。

中國現在發展比較穩定,以經濟為基礎,維穩治國。而對於非遺保護,提倡的方式比較公式化,內心強烈感到必要性的人相對比較少。鄭教授在國內看到的是,有一些精英知識份子,現在對於雅化的東西,追求得很厲害,因為生活素質大大提升了,就發現古代有很多高雅、美好的東西。「可是老百姓對於他們自己的東西呢?還是以賺錢糊口為第一位。香港很多基層的文化傳承,因為是跟宗教、宗族有關,有著深層意識的持續,保護的比較好。內地農村最近好一點,有很多人回家鄉去推廣地方特色,搞旅遊、建民宿,因為可以賺錢。很多老房子搞得很漂亮,有特殊地方風格的建築得以保留下來。」
「歷史有很強的反諷性,當人自己以為甚麼是真理的時候,其實時常不知道自己認識的片面性。可是歷史很長久,它的經驗會讓人認識到,有些東西恐怕不是硬推就可以成功的,所以它還會回頭。」鄭教授語重深長地說。

現在香港人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感很弱,要推廣非遺似乎更加困難,而非物質文化的傳承是會隨時代出現變化的。非遺教育的過程中,老師可以多指導學生探討一系列的問題,例如:非遺是甚麼?跟自己有甚麼關係?這裡就牽涉到自身的文化認同是怎麼一回事。如果不需要有文化認同,那麼該怎麼辦?如果不認同任何東西,那怎麼活?人在精神上是否需要這個東西?鄭教授認為學生可以從討論的過程中得到更多的啟發,認識自己的生命意義。
「要大家真切地感覺到非遺對社會的影響力,還有它對長遠的文化傳承的意義,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和堅持。推動文化教育,要循次漸進,在漫長的過程中偶爾會有抱怨和挫折感。可是你要我回顧,整體來說已經比以前好很多。」鄭教授娓娓道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