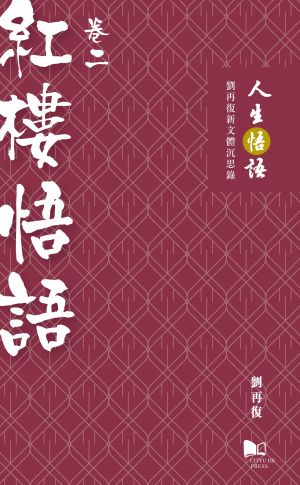我父親(劉再復)非常勤奮,數十年如一日地堅持「黎明即起」,每天早晨五點便開始寫作。從五點到九點,這是他的黃金時段,創造時刻。數十年的「一以貫之」,使他著作等身,僅中文書籍就出版了一百二十五種(五十多種原著,七十多種選本、增訂本、再版本)。我從讀北大開始,就喜歡他的片斷性思想札記,那時札記發表得並不多,但因我是「近水樓台」,所以還是讀了一些,比如《雨絲集》。出國之後,他思如泉湧,一發而不可收,竟然寫下了二千多段悟語(「獨語天涯」八百多段,「面壁沉思錄」四百多段,「《紅樓夢》悟語」六百多段,「《西遊記》三百悟」三百段,「雙典百感」一百段,各類人生悟語近一百段)。這些悟語,精粹凝煉,語短意長,每一段都有一個文眼,即思想之核。二千多則,可以視為「悟語庫」了。
我稱父親的悟語寫作為「新文體寫作」。所謂新文體,乃是指它不同於當下流行的小品、雜文、散文詩,也不同於隨想錄等文體。雜文較長,有思想、有敍事、有議論,而悟語則只有思想而沒有敍事與感慨。與散文詩相比,它又沒有抒情與節奏。與隨想錄相比,它顯得更為明心見性,完全沒有思辨過程,也可以說沒有邏輯過程。這種文體很適合於生活節奏快速的現代社會。我相信,那些忙碌又喜歡閱讀的智者與識者,肯定最歡迎這種文體,他們在工作的空隙中,在旅途的勞頓中,都可以選擇一些段落加以欣賞和思索,享受其中一些對世界、人類、歷史的詩意認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稱這些悟語為「新文體」是否恰當?可以討論。說它是「新」,乃是相對於流行的文體即論文、散文、雜文等,但如果放眼數千年的文學藝術史,我們還是可以發現,這種「思想片斷」的寫作曾經出現過。例如古羅馬著名的帝王哲學家馬可•奧理略(Marcus Aurelius)所寫的《沉思錄》(中文版由何懷宏先生所譯),便是他在軍旅勞頓中的哲學感悟,一段一段都是精彩的悟語。此書影響巨大,千年不衰,早已成為西方思想史上公認的名著。我覺得他寫的正是「悟語」。每一則都有思想,但沒有思辨過程。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和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也喜歡採用這種片斷式寫作來表述他們靈動的思想。魯迅的《熱風》,其文字形式正是尼采式的悟語。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霍拉斯•恩格道爾(Horace Engdahl)在他的著作《風格與幸福》(中文版由陳邁平先生所譯)中,有一章題為「有關碎片寫作的筆記」,專門論述「悟語」這一革命性文體,談到歷代西方文學家各式各樣的「碎片寫作」。他認為「碎片寫作」是對立於體系寫作的一種寫作。它不求邏輯建構,而是像精靈一樣四處遊蕩,這些表面無序的不連續的文字,「是在無數個體的中心生出來的」。恩格道爾有一段精彩的定義:「碎片寫作的決定可以讓不同思想區域之間的自由移動成為可能。諾瓦利斯(Novalis)談到過『精神的旅行藝術』,在他的筆記裏這種藝術採用永遠處在回到一切涉及精神的事物的返鄉形式。這是一部飛翔着的百科全書。」[1]
儘管悟語寫作、片斷寫作已有前例,但我父親能寫出這麼多的感悟之語,實在不容易。況且他又有新的創造,例如評述中國四大名著的悟語,便有許多新的眼光和新的思路,無論是對《紅樓夢》、《西遊記》的禮讚,還是對《水滸傳》、《三國演義》的文化批判,都可謂入木三分,不同一般。文學評論、文化批判也可通過悟語進行,而且可以超越文本和擊中要害,這的確是一種有意思的實驗。可以說,父親對碎片寫作的思維空間進行了先鋒性的拓展。他認為,在人文科學中,文學只代表廣度,歷史呈現深度,哲學則可代表高度,而碎片寫作也可以在此三維度上加以發展。從廣度上說,以往的碎片寫作多半着眼於人生遭際中的感受,倫理色彩較濃。從孔子的《論語》到奧理略的《沉思錄》以至尼采,皆是如此。但他加以擴展,把碎片寫作運用到文學批評、文化批評、國民性批評和人類性批評。文學批評如對《紅樓夢》中的人物分析;文化批評如〈西遊記三百悟〉講「禪而不相」、「禪而不宗」、「禪而不佛」等;國民性批評,如〈西遊記三百悟〉中的第二百九十八則和二百九十九則尖銳地批判了中國的國民性問題;人類性批評,如〈童心說〉涉及的是普遍的人性問題。從深度上說,悟語的深度來自他對歷史的認知與對世界的認知。歷史有表層結構,也有深層結構。深度主要是呈現於對深層歷史的認知和深層文學的認知。如〈雙典百感〉的第五十六則,揭露《三國演義》維護正統的旗號,實際上漢王朝已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美化劉備與抹黑曹操全是權術(騙人的把戲)。還有〈《紅樓夢》悟語二百則〉的第二百零五則,寫的並非歷史,但把文學的深度揭示出來了。至於他如何把碎片寫作推向哲學,看看〈紅樓哲學筆記三百則〉就明白了,其中每段都有一個小標題—無相哲學、自然的人化、情壓抑而生大夢、叩問人生究竟、色透空也透、立人之道、意象心學、棄表存深、通脫主體論、隨心哲學等—每一題都有哲學感悟,每一段均有所妙悟。在中國寫作史上,如此大規模地通過片斷寫作展示密集豐富的哲學思想,以前還沒有見過。
父親晚年近莊子和禪宗,他對自己在海外近三十年漂泊生活的領悟,以及對中國四大名著的重新闡釋,都採取「片斷悟語」的寫作形式,其實如同一段段「禪悟」,以心讀心,與古典名著裏的一個個靈魂對話,也同時與自己的多重主體對話,捕捉思想的精彩瞬間。他曾經這樣描述自己的悟語寫作:
在我心目中,「悟語」類似「隨想錄」與「散文詩」,有些「悟語」其實就是散文詩和隨想錄,但多數「悟語」還是不同於這兩者。隨想錄寫的是隨感,「悟語」寫的是悟感。所以每則悟語,一定會有所悟,有所「明心見性」之「覺」。隨想錄更接近《傳習錄》(王陽明),悟語更近《六祖壇經》(慧能)。與散文詩相比,「悟語」並不刻意追求文采和內在情韻,只追求思想見識,但某種情思較濃的「悟語」也有些文采,只是必須嚴格地掌握分寸,不可「以文勝質」,只剩下漂亮的空殼。[2]
我個人認為,父親的這種「新文體寫作」,跟他自一九八九年選擇海外漂流的「第二人生」有緊密的關係。這第二人生給他的最大收穫,就是獲得了內心的大自由,身心均得大自在。這種不再被政治權力、國家界限、世俗利益約束的內心大自由,不可能再用學院派的重體系、重邏輯、重理論的文學批評語言來表述,而必須找到實驗性更強、自由度更大的文體來承載他自由的心靈書寫,「悟語」或「碎片寫作」這種文體,給了他一種解放的形式,便於闡發一種屬於他自己的內心真實,而且他在瞬間感悟的真實都是他自身的多重個體的折射,於是,這種「新文體寫作」成了呈現他選擇的徹底的「心性本體論」的載體,如同他所說的:「佛就是心,心就是佛。佛不在寺廟裏,而在人的心靈裏。講的是徹底的心性本體論。慧能的《六祖壇經》說『自性迷,即是眾生;自性覺,即是佛』,所謂『覺』,就是心靈在瞬間抵達『真理』的某一境界,在心中與佛相逢,並與佛同一、合一。」[3]這種「新文體」寫作—碎片寫作、悟語寫作,是對個體「瞬間領悟」、「瞬間覺悟」的記錄,是飛翔的思緒,是流動的靈光,是精神的自由旅行。
卷一至卷四的「劉再復新文體沉思錄」有兩項基本內容。第一部分體現了父親在海外漂泊的歲月裏不停地尋找「家園」及尋找精神昄依的旅程。從前的地理意義上的故鄉消失了,他需要重新定義自己心目中的家園,於是他在碎片寫作中,一邊叩問歷史和家國,一邊叩問「我是誰」;一隻眼睛看世界、看歷史,另一隻眼睛看自我—看被粗暴的時代分割成碎片的自我;他一邊讀生命,另一邊讀死亡;他一邊讀東方,另一邊讀西方;他一方面重新找尋中西方文化相通的精神家園,另一方面又重新組合起一個多重的自我,有矛盾掙扎的自我,有回歸童心的自我,也有不斷超越的自我。這套新文體寫作的第二部分內容是重讀文學經典,也就是重讀中國四大古典名著:《紅樓夢》、《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傳》。用「片斷悟語書寫」闡釋中國四大古典名著的學者,恐怕父親是第一位,這種讀法既是一種文化批評,又是一種帶有啟迪性的文體創造。無論是討論小說人物,還是討論小說主題、文化內涵,父親其實最重視的還是這些小說塑造的「心靈世界」,以及這一心靈世界對中國國民性的深刻影響。我在閱讀父親的這四卷「新文體沉思錄」時,認為父親用「片斷寫作」打破了傳統文學形式的界限,放下散文詩、文學評論、哲學思緒等形式阻隔,融合不同學科領域的特長和內涵,使得不同的表述形式和感悟處於一種自由的不規則、不系統的狀態,讓他的語言在稠密的思想中,撲扇着翅膀在空中滑翔,傳達了他聞的道、悟的道,傳達着普世哲學,也承載着中國當下幾乎喪失的人文精神。
帝王哲學家馬可•奧理略所寫的《沉思錄》已過去近兩千年了,他大約沒想到,今日的世界,人類的生活更為緊張,節奏更為快速,人們更需要這種言簡意繁的文字。我父親的這一新文體寫作,居然在不經意間與現在的微博、微信寫作有了一些外在的聯繫,就像他寫的:「老子所講的『大音希聲』,乃是對語言的終極性叩問。真正卓越的聲音是謙卑的、低調的,甚至是無言的。中國的詩句『此時無聲勝有聲』,乃是真理。最美的音樂往往是在兩個音符之間的過渡,此時沉靜的瞬間可以聽到萬籟的共鳴。」[4]雖然父親的新文體寫作彷彿是「微言」,可是它讓我們以微見大,感悟生命的終極意義。它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既是文學評論,又是文學創作;既是哲學的,又是文學的。它是對概念的放逐,是一種解放了的語言和文學實踐,是一種「心生命」。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的社長朱國斌先生、副社長陳家揚先生,慧眼獨具,深知悟語的價值,支持我父親的寫作試驗,這不僅鼓勵了父親,也鼓勵了我。我一直認為,文章與書籍是人寫的,人性極為豐富,文章也可有千種萬種,不必拘於幾種樣式。碎片式的寫作,悟語的嘗試,肯定也是一種路子。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的決定與支持,使我的思想更為開放,視野更加拓展,為此,我和父親一樣,都心存感激。
劉劍梅
二○一八年寫於香港清水灣
Volume V-Dialogue in the Human Realm
Product Name in original language
卷五:共悟人間
HKD128.00
In stock
巻五為作者與大女兒劉劍梅身在異地的書信紀錄。這些書信有別於一般父女閒話家常、噓寒問暖的內容,反而是深入地探討了古今中外的文學、哲學、人生等問題,二人談學問知識之餘,又側重心靈的交流,避免了一般說教的「父女相」,字裏行間流露着父女之間的温情和親切感。正如金庸所薦:「即使你不認識兩位作者,看這本書也會樂在其中,因其中談及的是文學與人生……」
ISBN
978-962-937-439-6
Pub. Date
Jul 19, 2019
Weight
0.8kg
Paperback
424 pages
Dimension
130 x
210 mm
Subjects
「新文體寫作」的意義
第一輯 共鑒滄桑
第二輯 共悟人間(上)
第三輯 共悟人間(下)
附錄一: 金庸談《共悟人間》
附錄二: 《兩地書寫》作者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