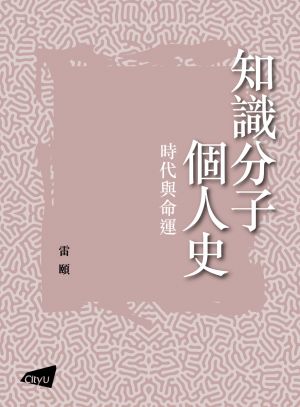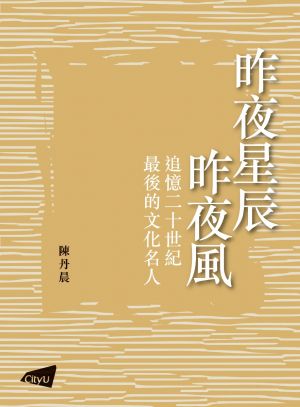The Plight of China's Intellectuals—From Past to Present
Product Name in original language
中國知識分子的困境
HKD108.00
In stock
無論是中國古代的士大夫,還是現代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曾命運曲折,經歷不同的坎坷,常處於困境中。
中國自春秋戰國時期便有「士」,他們具有強烈的責任感,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他們出謀獻策,儘管常得不到君主的賞識和重用,卻樹立了獨立的士風,在百家爭鳴中創建了各自的學說,造就中華民族的文化底蘊。自秦統一中國後,經過二千多年封閉的皇權專制制度,中國讀書人經歷了曲折崎嶇的道路。及至晚清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在這封閉的社會打開了一個口子,現代知識分子經過西學東漸,受到啟蒙,有了新的觀念和思想。他們有強烈的愛國心,對各自的專業鞠躬盡瘁,著書立說,以振興中華為己任,為社會正義奔走吶喊,卻多數壯志難酬,命途多舛,頻頻陷入困境,甚至難保個人的獨立與尊嚴。
本書收集了資中筠先生自1980年寫的文章,捋清了傳統士大夫及當今知識分子的演變和異同,細述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也道出了「啟蒙」前後,知識分子的思想精神、社會文化的轉變。現今教育普及、科技發達,但社會道德觀念、人民素質、文化修養卻似在逐漸倒退,近年「愛國」口號下所滋長的虛驕之氣和狹隘的排外情緒,更讓作者感到憂心。中國有「識」之士,是否正進入另一個困境?
中國自春秋戰國時期便有「士」,他們具有強烈的責任感,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他們出謀獻策,儘管常得不到君主的賞識和重用,卻樹立了獨立的士風,在百家爭鳴中創建了各自的學說,造就中華民族的文化底蘊。自秦統一中國後,經過二千多年封閉的皇權專制制度,中國讀書人經歷了曲折崎嶇的道路。及至晚清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在這封閉的社會打開了一個口子,現代知識分子經過西學東漸,受到啟蒙,有了新的觀念和思想。他們有強烈的愛國心,對各自的專業鞠躬盡瘁,著書立說,以振興中華為己任,為社會正義奔走吶喊,卻多數壯志難酬,命途多舛,頻頻陷入困境,甚至難保個人的獨立與尊嚴。
本書收集了資中筠先生自1980年寫的文章,捋清了傳統士大夫及當今知識分子的演變和異同,細述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也道出了「啟蒙」前後,知識分子的思想精神、社會文化的轉變。現今教育普及、科技發達,但社會道德觀念、人民素質、文化修養卻似在逐漸倒退,近年「愛國」口號下所滋長的虛驕之氣和狹隘的排外情緒,更讓作者感到憂心。中國有「識」之士,是否正進入另一個困境?
ISBN
978-962-937-444-0
Pub. Date
Jan 1, 2020
Weight
0.8kg
Paperback
452 pages
Dimension
140 x
190 mm
Subjects
Book Review
應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之約,出一本以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為主的文集。檢點幾十年來與此有關的文字,集結於此。除了直接與讀書人有關的文章外,還有一些間接有關的如愛國、啟蒙、歷史觀、婦女觀等等,以及少量無法分類的雜文,共得四十三篇,這些文章成文的時間跨度近四十年,最早發表於1980年,最近的一篇殺青於2019年,一部分過去散見於各種報刊,一部分是今年來發於我的微信公號。有幾篇從未發表過。這個跨度剛好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時期和我自己思想陸續解放,取得相對寫作自由的時期相吻合。本書按文章內容大致分為三部分,各部分文章按首發時間以倒序方式編排,從今天回看昨日。
本人以筆耕為業,實際上是半百以後才開始。前半生所寫文字都是奉命之作,多為「內部」報告,偶然以他人名義公開發表,也多為應景文章,不值得追認。我筆歸我有已是知命之年。對我這個半生為馴服工具的人說來,發現原來這支筆還能屬於自己,可以這樣來用,是一大解放。前期主要是專業研究的學術著作。在「正業」之外興之所至寫點東西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當然是與當時的開放形勢分不開的。開始只是偶一為之,且多為讀書心得,後來逐漸欲罷不能,大量寫作始於九十年代,特別是正式退休之後。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諸筆端,沒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擺脫了命題作文之累。
我本無「倚馬才」,以產量論,留下的文字實在不算多。自1995年起陸續出了幾本文集。2011年重新整理三十年來的文字,出了《資中筠自選集》,按題材分,共得五卷,取名為:《感時憂世》、《士人風骨》、《坐觀天下》、《不盡之思》、《閑情記美》。我一向認為自己的作品是小眾讀物,讀者面不會太廣。《自選集》受到的讀者歡迎是出乎我意料的。此書一再重印,並被各種書評刊物評為「好書」,還獲了不少獎。自己的文字多一些讀者,當然總是開心的。更令我欣慰的是,這些代表了我的思考、言出於衷的的看法,雖往往與主流宣傳不合,卻得到越來越多的讀者認同,而且是不同年齡段的,包括很多年輕人,感到吾道不孤。這也許與互聯網的傳播力有關。我沒有開過微博。2015年之後,在年輕朋友的慫恿下,「與時俱進」地開了微信公號,又得到熱心朋友自告奮勇為之編輯,在上面發表了不少新舊文章。而且關注度日益上升。在文網日益收緊的形勢下,五卷本的《自選集》現已絕版;在微信上發文也阻力重重。但是一息尚存,總不能停止思考,所以每有心得,還是忍不住要寫出來,存之電腦,只問耕耘,不問收穫。
本人以筆耕為業,實際上是半百以後才開始。前半生所寫文字都是奉命之作,多為「內部」報告,偶然以他人名義公開發表,也多為應景文章,不值得追認。我筆歸我有已是知命之年。對我這個半生為馴服工具的人說來,發現原來這支筆還能屬於自己,可以這樣來用,是一大解放。前期主要是專業研究的學術著作。在「正業」之外興之所至寫點東西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當然是與當時的開放形勢分不開的。開始只是偶一為之,且多為讀書心得,後來逐漸欲罷不能,大量寫作始於九十年代,特別是正式退休之後。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諸筆端,沒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擺脫了命題作文之累。
我本無「倚馬才」,以產量論,留下的文字實在不算多。自1995年起陸續出了幾本文集。2011年重新整理三十年來的文字,出了《資中筠自選集》,按題材分,共得五卷,取名為:《感時憂世》、《士人風骨》、《坐觀天下》、《不盡之思》、《閑情記美》。我一向認為自己的作品是小眾讀物,讀者面不會太廣。《自選集》受到的讀者歡迎是出乎我意料的。此書一再重印,並被各種書評刊物評為「好書」,還獲了不少獎。自己的文字多一些讀者,當然總是開心的。更令我欣慰的是,這些代表了我的思考、言出於衷的的看法,雖往往與主流宣傳不合,卻得到越來越多的讀者認同,而且是不同年齡段的,包括很多年輕人,感到吾道不孤。這也許與互聯網的傳播力有關。我沒有開過微博。2015年之後,在年輕朋友的慫恿下,「與時俱進」地開了微信公號,又得到熱心朋友自告奮勇為之編輯,在上面發表了不少新舊文章。而且關注度日益上升。在文網日益收緊的形勢下,五卷本的《自選集》現已絕版;在微信上發文也阻力重重。但是一息尚存,總不能停止思考,所以每有心得,還是忍不住要寫出來,存之電腦,只問耕耘,不問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