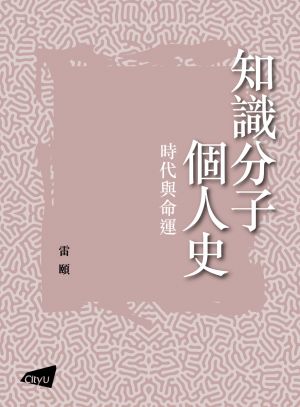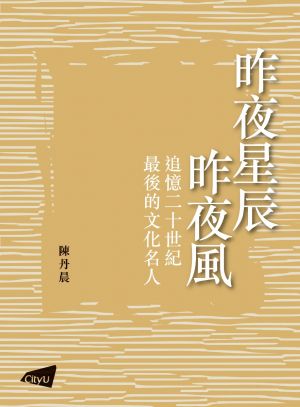Rethinking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European History and East-West Culture
Product Name in original language
看的是歐洲• 想的是中國—中國知識分子與中西文化
HKD158.00
In stock
「中西之交,乃是古今之異。」在中國的文化史上,中國的思想根源來自人生哲學,包括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少有自然哲學。古代的士大夫一心希望當官,為政治服務;而西方國家的思想根源,來自科學和哲學豐富的希臘文化及希伯來文化,並逐漸形成了西方文明。
可是此情況在十九世紀西洋文明進入中國後出現了轉變,尤其在「五四」時期,不少中國的知識分子,到西方國家留學,學習西學,西方的政治學、哲學、社會學、自然科學也如雨後春筍進入中國,中國知識分子並曾經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權;可是後來的政治鬥爭、階級鬥爭、文化大革命,知識分子遭到批鬥,中國把接受西方文明的大門關上,同一時間中國文明也一下子倒退了。
本書作者長期研究歐洲史,從中西國家的來源,社會形態的發展,文化思想的差異,反思中國的文明發展,並回顧歷來研究中西文化的中國知識分子,了解他們的西學研究,思考中國的文明發展為何不同於西方國家。
可是此情況在十九世紀西洋文明進入中國後出現了轉變,尤其在「五四」時期,不少中國的知識分子,到西方國家留學,學習西學,西方的政治學、哲學、社會學、自然科學也如雨後春筍進入中國,中國知識分子並曾經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權;可是後來的政治鬥爭、階級鬥爭、文化大革命,知識分子遭到批鬥,中國把接受西方文明的大門關上,同一時間中國文明也一下子倒退了。
本書作者長期研究歐洲史,從中西國家的來源,社會形態的發展,文化思想的差異,反思中國的文明發展,並回顧歷來研究中西文化的中國知識分子,了解他們的西學研究,思考中國的文明發展為何不同於西方國家。
ISBN
978-962-937-443-3
Pub. Date
Jul 1, 2020
Weight
0.5kg
Paperback
264 pages
Dimension
140 x
190 mm
Subjects
Book Review
我為甚麼要進入文明史的研究
二十多年前,我在寫《戰後西歐國際關係》時,即時想到一個問題:所謂「國際關係」或「國際問題」,放到社會科學裏,能不能算做一門「獨立的學科」?當時初建西歐研究所時,大家的共識是把研究的時間範圍設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而實際上,大家越來越把關注點放在當前的「熱門」話題上,只跟蹤眼前發生的事情。於是我產生了一種印象:這似乎等於把新華社以及當時所能看到的外國通訊社的消息(大部分又都能在《參考資料》上看到)當作基本材料,編寫成各類專題性的文字,這樣的工作至多是一種資料的整理,很難說是學術性的、理論性的研究。
我還覺得,作為社會科學的國際問題研究,應該不同於外交部的國際問題研究所那樣的實用性的工作。所以,在我的腦子裏一直有一個「在社科院裏國際問題的研究應該是怎樣的」的問號。
對於我個人來說,從寫《戰後西歐國際關係》時起,就越來越覺得,國際問題的研究必須和社會科學的「五大支柱」即文、史、哲、政、經結合起來,或者說需要有這些基本學科的滋養和支撐。我曾同當時負責領導「國際片」的社科院已故副院長李慎之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很贊同我的看法。他說:「研究國際問題的人,首先應該是『通才』。」還說:「研究者需有文史方面的修養,而『國際』則代表是一種廣闊的世界眼光。」後來我寫了一篇〈拓寬國際問題研究的視野〉,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國際問題研究,要搞出水平來,是一件很困難的事。這有兩層意思。其一,學者本人的文化素養問題,一個中國學者需要中西兼顧。國際問題研究是研究世界上的事,但是一個中國學者不可不通曉中國的歷史文化、中國的文獻、中國的哲學。嚴復曾經抱怨那時中國留學生只懂西文和洋概念,不懂中學,結果或者成為西人的羽翼,或者學得些屠龍之技,回來一無可用,結果不過是包裝金光熠熠,實際上沒有多少實貨的傳聲筒。過去看喬冠華、蕭乾等人寫的國際小品,覺得很耐看,不落俗套,原因之一就是他們有很深的文化素養和見識。
其二,「國際關係」是人類社會或文明發展史中的屬於國際政治的「零部件」,必須把它放在世界文明史的大框架裏去考察。脫離了文明和社會,就只剩下了浮在表面上的關係。例如研究歐洲,它本身就是一個文化概念,或文明概念。一個研究者應該有歐洲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發展方面的儘可能充分的知識和思想準備。我在幾乎快寫完《戰後西歐國際關係》時便開始考慮歐洲的文明問題,或者是轉向歐洲文明範圍內的問題,於是便脫離了單純跟蹤眼前現實的路數。
正是在這個時候,資深編輯鄧蜀生先生受浙江人民出版社之託組織一套「當代世界名人傳記叢書」,約我寫《戴高樂》和《撒切爾夫人》兩本。基於上述的研究思路,我把戴高樂和撒切爾夫人(編按:Margaret Thatcher,港譯戴卓爾夫人)既分別放在法蘭西和不列顛歷史文明的傳統裏,又放在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裏,通過這兩個人傳達兩種文明。
1984年6月,我訪問法國臨近結束時,拿到了一份請帖,請我參加巴黎大學「爭取獨立與和平論壇」討論會。討論會的總題目是「歐洲:文化的內在同一性和現代性」,副題是「同一性中的多樣性;多樣性中的同一性」。我覺得新鮮,便去參加了。到會的除法國學者外,有英國、德國、意大利、希臘等國的學者,我沒有發現除我以外的非歐洲人。討論會分為三個小組,主題分別是:文化的內在同一性;民主、和平和歐洲建設;歐洲面臨的新挑戰。我走馬觀花,三個小組的討論都聽了一些。發言的人從不同角度談歐洲有哪些有利於歐洲聯合的因素,有哪些內外因素使它們非聯合起來不可。同時也有許多人慷慨激昂地講了有哪些障礙和難題使歐洲依然無法聯合。總之是從歐洲自身出發談歐洲的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問題。當時正值西方一些報刊聳人聽聞地大談「歐洲的衰落」,再加上新科技革命的壓力和「重點轉向太平洋」之議,「歐洲怎麼辦」的問題簡直無法迴避。我聽到的發言幾乎無例外地都說腦子裏要有個「歐洲觀念」,即超越民族界限的「歐洲觀念」。
何謂「歐洲觀念」?到圖書館一看,講這個問題的書真不少,我一目十行地瀏覽了一本法國史學家寫的《歷史中的歐洲觀念》,又看了一本《歐洲的先行者》。後來在倫敦的圖書館狼吞虎嚥地又看了幾本書。這些書內容豐富,但散得很,一路說開去,對於「歐洲觀念」這個概念本身,率皆語焉不詳。我想:「歐洲觀念」大概就是巴黎論壇上說的「歐洲人何以為歐洲人」的意思吧。
然而,所謂歐洲畢竟包含許多「民族國家」。因此「歐洲觀念」勢必含有兩層意義—既是歐洲的,又是民族的。
某個星期天,我到倫敦塔去遊覽,在一條長椅上歇腳,旁邊坐着一個英國老者,我們漫談起歐洲人的不同特色來。這時走過一群穿紅着綠的青年遊客。老者指着他們說:「如果他們不是講的某種歐洲的民族語言,簡直分辨不出他們是哪國人;都是一個樣兒,看不出民族來。」
不過,法裔美國學者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對我說:「別小看了英吉利海峽,一水之隔,民情迥異!」
我多次問過一些英國學者,今天的英國人是否仍然認同當年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一個觀點,即英國和歐陸的關係是「with」而不是「of」。他們說問題提得微妙,英國人是歐羅巴人,但不是大陸的歐洲人;切莫忽視了歷史傳統的差異。
當今世界,由於科學技術的發達,人的時空觀念已經大大改變;用不了一個小時的飛行就可以從巴黎到倫敦;特別快車可以一天穿過幾個國家。無論有沒有一個組織起來的「共同市場」,這個「市場」自然就在那裏。「歐洲聯盟」乃是歷史發展的自然邏輯的產物。青年一代對於半個世紀前的「戰後」情況,只在書本上看過,或聽老人們講過,如今那理解已大不相同。當代法國人和德國人相處的心理狀態和相互關係,與普法戰爭以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情形相比,早已起了根本變化。法國中學生對阿爾封斯‧都德(Alphonse Daudet)舉世聞名的短篇小說《最後的一課》(La Dernière Classe)的感受和體會,肯定不會像他們的前輩那樣。歐洲人的相互「趨同」和「認同」意識,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代了歷史上民族「對立」的情緒。
然而,當你看一場歐洲足球賽的時候,觀眾席上沸騰的激情,人心的向背,會使你突然發現歐洲的民族主義的感情猶如無法抑制的洪水。更不要說在涉及民族利益的根本問題時,只需根據發言人的談吐和舉止,就一下子能判斷出是哪個國家的立場了。
所以,「歐洲觀念」反映的是兩種含義的交織:歐洲有自己的「認同性」,歐洲主義者側重這一面;歐洲又是不同民族國家構成的,民族主義者堅持這一面。歐洲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悖論是歐洲的常態,綜合在「歐洲觀念」裏。
歐洲文明史上的時分時合,有「一」有「多」,分中有合,合中有分,是了解歐洲歷史哲學的一個線索。雖然有失淺顯,但它是經過我自己的探索而抽出來的一條線。於是我先是把粗淺所得,寫成了一篇文章,題目叫〈「歐洲統一」觀念的歷史哲學論綱〉,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上,並受到了一些朋友的注意。他們建議我把這篇文章擴大成一本書,這樣可以說就有了我研究歐洲文明史的第一本書,即《「歐洲觀念」的歷史哲學》。經過若干年,認識在不斷發展,於是在上個世紀末又有了我和周弘合著的《歐洲文明擴張史》和最近出版的後者的增訂本《歐洲文明的進程》。也許今年年初,我去年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講課紀錄稿也將輯印成書,書名《歐洲文明史論十五講》。在後幾本書裏,我都涉及了我晚年所歸結的一個思索命題:「歐洲何以為歐洲?中國何以為中國?」這肯定是我有生之年作不完的文章。
我還覺得,作為社會科學的國際問題研究,應該不同於外交部的國際問題研究所那樣的實用性的工作。所以,在我的腦子裏一直有一個「在社科院裏國際問題的研究應該是怎樣的」的問號。
對於我個人來說,從寫《戰後西歐國際關係》時起,就越來越覺得,國際問題的研究必須和社會科學的「五大支柱」即文、史、哲、政、經結合起來,或者說需要有這些基本學科的滋養和支撐。我曾同當時負責領導「國際片」的社科院已故副院長李慎之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很贊同我的看法。他說:「研究國際問題的人,首先應該是『通才』。」還說:「研究者需有文史方面的修養,而『國際』則代表是一種廣闊的世界眼光。」後來我寫了一篇〈拓寬國際問題研究的視野〉,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國際問題研究,要搞出水平來,是一件很困難的事。這有兩層意思。其一,學者本人的文化素養問題,一個中國學者需要中西兼顧。國際問題研究是研究世界上的事,但是一個中國學者不可不通曉中國的歷史文化、中國的文獻、中國的哲學。嚴復曾經抱怨那時中國留學生只懂西文和洋概念,不懂中學,結果或者成為西人的羽翼,或者學得些屠龍之技,回來一無可用,結果不過是包裝金光熠熠,實際上沒有多少實貨的傳聲筒。過去看喬冠華、蕭乾等人寫的國際小品,覺得很耐看,不落俗套,原因之一就是他們有很深的文化素養和見識。
其二,「國際關係」是人類社會或文明發展史中的屬於國際政治的「零部件」,必須把它放在世界文明史的大框架裏去考察。脫離了文明和社會,就只剩下了浮在表面上的關係。例如研究歐洲,它本身就是一個文化概念,或文明概念。一個研究者應該有歐洲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發展方面的儘可能充分的知識和思想準備。我在幾乎快寫完《戰後西歐國際關係》時便開始考慮歐洲的文明問題,或者是轉向歐洲文明範圍內的問題,於是便脫離了單純跟蹤眼前現實的路數。
正是在這個時候,資深編輯鄧蜀生先生受浙江人民出版社之託組織一套「當代世界名人傳記叢書」,約我寫《戴高樂》和《撒切爾夫人》兩本。基於上述的研究思路,我把戴高樂和撒切爾夫人(編按:Margaret Thatcher,港譯戴卓爾夫人)既分別放在法蘭西和不列顛歷史文明的傳統裏,又放在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裏,通過這兩個人傳達兩種文明。
1984年6月,我訪問法國臨近結束時,拿到了一份請帖,請我參加巴黎大學「爭取獨立與和平論壇」討論會。討論會的總題目是「歐洲:文化的內在同一性和現代性」,副題是「同一性中的多樣性;多樣性中的同一性」。我覺得新鮮,便去參加了。到會的除法國學者外,有英國、德國、意大利、希臘等國的學者,我沒有發現除我以外的非歐洲人。討論會分為三個小組,主題分別是:文化的內在同一性;民主、和平和歐洲建設;歐洲面臨的新挑戰。我走馬觀花,三個小組的討論都聽了一些。發言的人從不同角度談歐洲有哪些有利於歐洲聯合的因素,有哪些內外因素使它們非聯合起來不可。同時也有許多人慷慨激昂地講了有哪些障礙和難題使歐洲依然無法聯合。總之是從歐洲自身出發談歐洲的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問題。當時正值西方一些報刊聳人聽聞地大談「歐洲的衰落」,再加上新科技革命的壓力和「重點轉向太平洋」之議,「歐洲怎麼辦」的問題簡直無法迴避。我聽到的發言幾乎無例外地都說腦子裏要有個「歐洲觀念」,即超越民族界限的「歐洲觀念」。
何謂「歐洲觀念」?到圖書館一看,講這個問題的書真不少,我一目十行地瀏覽了一本法國史學家寫的《歷史中的歐洲觀念》,又看了一本《歐洲的先行者》。後來在倫敦的圖書館狼吞虎嚥地又看了幾本書。這些書內容豐富,但散得很,一路說開去,對於「歐洲觀念」這個概念本身,率皆語焉不詳。我想:「歐洲觀念」大概就是巴黎論壇上說的「歐洲人何以為歐洲人」的意思吧。
然而,所謂歐洲畢竟包含許多「民族國家」。因此「歐洲觀念」勢必含有兩層意義—既是歐洲的,又是民族的。
某個星期天,我到倫敦塔去遊覽,在一條長椅上歇腳,旁邊坐着一個英國老者,我們漫談起歐洲人的不同特色來。這時走過一群穿紅着綠的青年遊客。老者指着他們說:「如果他們不是講的某種歐洲的民族語言,簡直分辨不出他們是哪國人;都是一個樣兒,看不出民族來。」
不過,法裔美國學者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對我說:「別小看了英吉利海峽,一水之隔,民情迥異!」
我多次問過一些英國學者,今天的英國人是否仍然認同當年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一個觀點,即英國和歐陸的關係是「with」而不是「of」。他們說問題提得微妙,英國人是歐羅巴人,但不是大陸的歐洲人;切莫忽視了歷史傳統的差異。
當今世界,由於科學技術的發達,人的時空觀念已經大大改變;用不了一個小時的飛行就可以從巴黎到倫敦;特別快車可以一天穿過幾個國家。無論有沒有一個組織起來的「共同市場」,這個「市場」自然就在那裏。「歐洲聯盟」乃是歷史發展的自然邏輯的產物。青年一代對於半個世紀前的「戰後」情況,只在書本上看過,或聽老人們講過,如今那理解已大不相同。當代法國人和德國人相處的心理狀態和相互關係,與普法戰爭以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情形相比,早已起了根本變化。法國中學生對阿爾封斯‧都德(Alphonse Daudet)舉世聞名的短篇小說《最後的一課》(La Dernière Classe)的感受和體會,肯定不會像他們的前輩那樣。歐洲人的相互「趨同」和「認同」意識,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代了歷史上民族「對立」的情緒。
然而,當你看一場歐洲足球賽的時候,觀眾席上沸騰的激情,人心的向背,會使你突然發現歐洲的民族主義的感情猶如無法抑制的洪水。更不要說在涉及民族利益的根本問題時,只需根據發言人的談吐和舉止,就一下子能判斷出是哪個國家的立場了。
所以,「歐洲觀念」反映的是兩種含義的交織:歐洲有自己的「認同性」,歐洲主義者側重這一面;歐洲又是不同民族國家構成的,民族主義者堅持這一面。歐洲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悖論是歐洲的常態,綜合在「歐洲觀念」裏。
歐洲文明史上的時分時合,有「一」有「多」,分中有合,合中有分,是了解歐洲歷史哲學的一個線索。雖然有失淺顯,但它是經過我自己的探索而抽出來的一條線。於是我先是把粗淺所得,寫成了一篇文章,題目叫〈「歐洲統一」觀念的歷史哲學論綱〉,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上,並受到了一些朋友的注意。他們建議我把這篇文章擴大成一本書,這樣可以說就有了我研究歐洲文明史的第一本書,即《「歐洲觀念」的歷史哲學》。經過若干年,認識在不斷發展,於是在上個世紀末又有了我和周弘合著的《歐洲文明擴張史》和最近出版的後者的增訂本《歐洲文明的進程》。也許今年年初,我去年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講課紀錄稿也將輯印成書,書名《歐洲文明史論十五講》。在後幾本書裏,我都涉及了我晚年所歸結的一個思索命題:「歐洲何以為歐洲?中國何以為中國?」這肯定是我有生之年作不完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