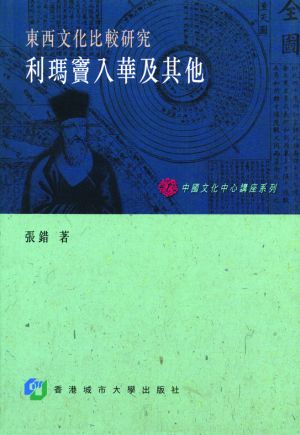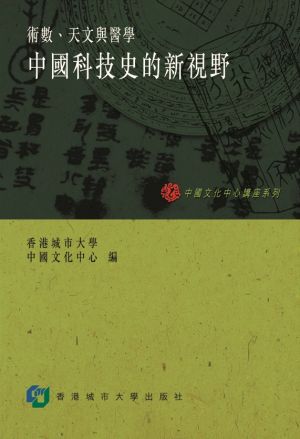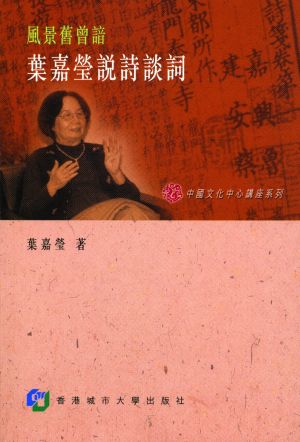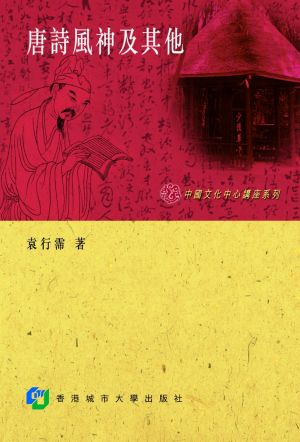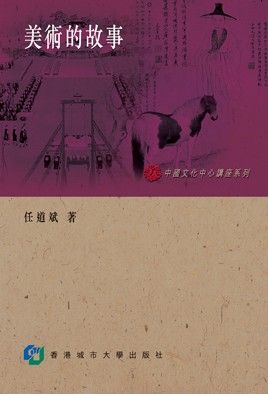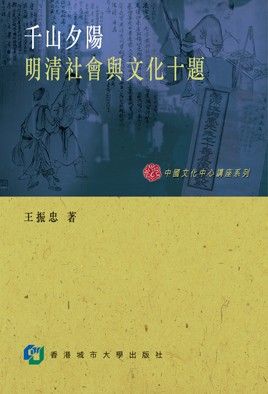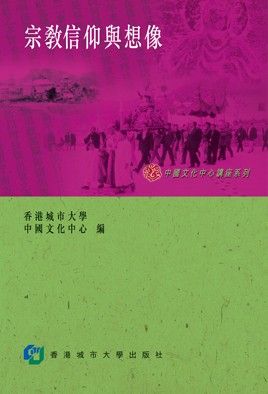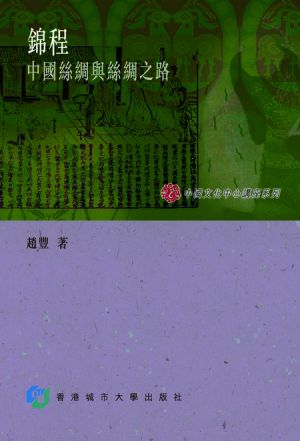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在規劃大學必修的中國文化課程之時,決定設立文化講座一項,延請海內外名家碩儒,為學生舉辦專題講座,內容反映當前學術界的最新成果,但講法卻要深入淺出。在安排講座之時,逐漸就會浮現一系列的相關專題,「歷史地理」就是其中之一。
我前後從國內邀請了一批歷史地理學的專家,講授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的不同側面,累積起來,就成了這一本書。
為了提醒同學的注意,我還在《城市新語》這個專欄中,寫過一篇小文章,以輕鬆的筆調談論歷史地理學的研究領域及方向,並戲稱之為「歷史舞台學」。這篇小文有點趣味,茲引如下,以代前言:
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近來請了好幾位歷史地理學家,做了一系列的講座。同學們不知道「歷史地理學」是什麼,就問,歷史地理學是不是歷史加地理,又講歷史又講地理?
我想起小學的時候,有門課叫「史地」,真的是又講歷史又講地理,不過卻分做兩截,講歷史時不講地理,講地理時不講歷史,倒是經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我們小學生可慘了,背完歷史人名地名,再背民國時期各省縣市地名交通物產,好像是西西弗斯推磐石上山一樣,無休無止又無聊,而且永無間斷。
歷史地理學是門跨學科的學問,一時還不容易講清楚。有位講者就打了個比方,說歷史學研究的是歷史上的人物與事件及其因果關係,歷史地理學則是研究這些人物與事件的舞台。 我後來與他說笑,就說這門學問可以改稱「歷史舞台學」或「歷史劇場學」。
說笑歸說笑,卻想起了楊絳的一篇散文,寫她1933年初秋,與錢穆先生一同搭火車,由蘇州赴北京的情景。其中一段很有趣:
車過蚌埠後,窗外一片荒涼,沒有山,沒有水,沒有樹,沒有庄稼,沒有房屋,只是綿延起伏的大土墩子。火車走了好久好久,窗外景色不改。我嘆氣說:「這段路最乏味了。」賓四先生說:「此古戰場也。」經他這麼說,歷史給地理染上了顏色,眼前的景物頓時改觀。我對綿延多少里的土墩子發生了很大的興趣。賓四先生對我講,那裏可以安營(忘了是高處還是低處),那裡可以衝殺。盡管戰死的老百姓朽骨已枯,磷火都曬乾了,我還不免油然起了吊古之情,直到「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在望,才離開這片遼闊的「古戰場」。
這似乎就是「歷史舞台學」的最佳注腳,希望同學們聽了講座之後,也能改觀。
鄭培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