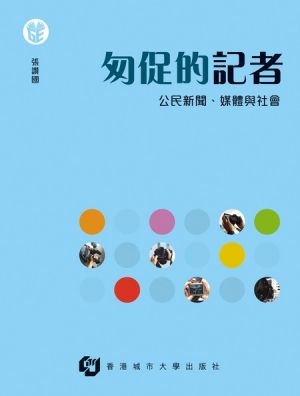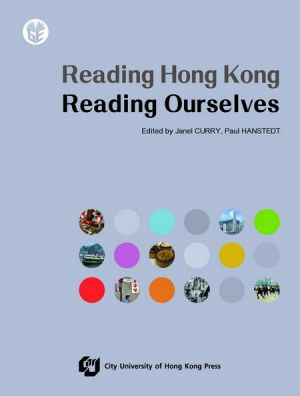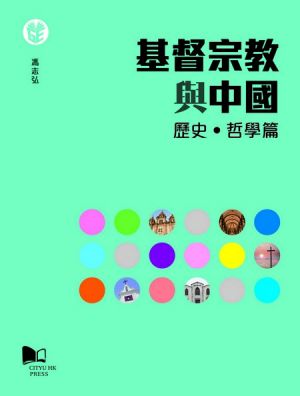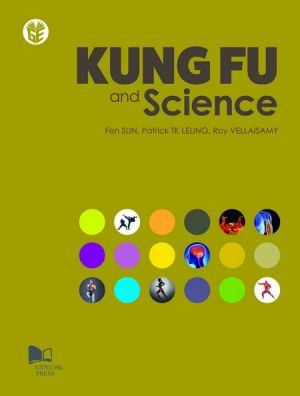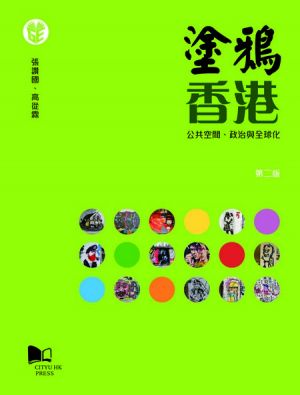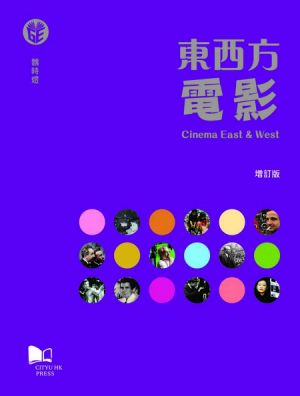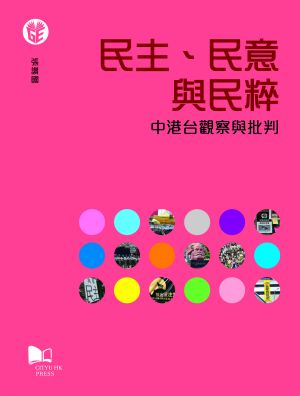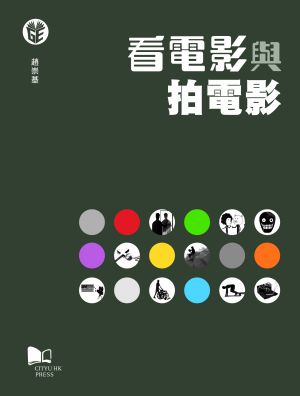Christianity and China: A Cultural Perspective
Product Name in original language
基督宗教與中國 (文化。藝術篇)
HKD120.00
In stock
唐代至今,「中國文化」與「基督宗教」的衝擊與交匯,始終是中西文化融合最令人摸不着的一環,世人仍鍥而不捨地追尋種種爭論的理想答案。對於傳教士和華人基督徒來說,中西藝術的「美」和他們信仰的「道」,有何關係?「審美」是否一種與生俱來的能力,以致不論文化背景,我們都有相對一致的「美」的共識?還是,有些「美麗」,必須首先認同潛藏其中的「道」,才能企及?
本書為《基督宗教與中國:歷史‧哲學篇》的姊妹篇,書名中的「文化」、「藝術」,與前篇的「歷史」、「哲學」相對分明。但兩部著作在作者筆下有許多心意是相通的。在不假設基督宗教可信與否,亦不採用無神論的前提下,作者透過剖析中國的文史哲藝與西方思維,深入爬梳各種古今材料,以思考文化、歷史、哲學等角度,訴說出「中國」與「基督宗教」在文化藝術的相遇及其現象,實事求是討論問題。
本書的內容跨度較廣,時間跨度長(明代以迄當代),就其骨架而言,本書先從「溯源」的宏觀論述,發展為專研文化難題;接着由文化進入藝術,又由「藝術」,回歸美學與文化相融或相抗的課題,希望藉此兼及文與藝、宏觀與微觀、專題與綜論、交流與衝突等不同向度,在較少的篇幅中呈現豐富的意義,適合作為人文學科的入門書籍之用。
ISBN
978-962-937-264-4
Pub. Date
Jul 1, 2016
Weight
0.51kg
Paperback
348 pages
Dimension
159 x
210 mm
Subjects
馮志弘:
寫作本書的時候,我覺得快樂。
這種快樂,就像19年前一樣—那是1997年12月的一個下午,我是個大學一年級生,當天早上,我剛完成「大學生涯」第一次期終試,真好!考試結束,可以跑圖書館了。到圖書館幹甚麼呢?我想知道一個「問題」的「答案」—
五代(907–960)時期事奉四朝、十帝的馮道(882–954),他對自己評價很高,自認「孝於家……『忠於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
馮道說:他自己「忠於國」—說這話的時候,他將近70歲,已經侍奉過三個朝代。
相反,北宋歐陽修(1007–1072)認為屢次「變節」的馮道,「可謂無廉恥者」。對於同一個人物,評價為何如此不同?馮道根據甚麼標準,在侍奉多朝以後仍然認為自己「忠於國」;歐陽修又根據甚麼準則,批評馮道「無恥」?
這不是哪個科目或哪一位老師給我的課業,只是我閒時閱讀想不通的事情—我想知道答案,更難以遏止自己的好奇心。於是,在1997年聖誕假期,我用了半月時間,寫了一篇只給幾個人看的文章,回答「如何評價馮道」的問題。我記得,當我用家中「噴墨式打印機」列印文稿,看着文章艱難地從打印機隙縫匍匐出來的時候,我很快樂。
後來我才知道,古今學者早就分析過這問題呢。而現在,我那篇「少作」都不知道跑哪裏去了。雖然如此,2007年我在香港城市大學講授「中國思想與文學」科目時,我還是偷偷把當年的念頭放在講義裏,專門以馮道和王安石(1021–1086)為例,分析「中國古代評價人物的標準」,以此作為自己學習旅途的紀念。我私下認為,這篇我已找不回的文章,是我「學術生命」的起點。或者說:當時的「快樂」,是我從此走上學術道路最大的理由。
讀書應該快樂,我們有時候居然會輕易忘記這一點。我想通過「通識科目」(城大稱為「精進教育Gateway Education」),讓同學和自己找回這種樂趣。
當然我們面對的問題是:有些人覺得「通識科目」與自己的「專業」無關—某某主修商業、生物、電子工程,為甚麼要他們認識「基督宗教與中國」?但小時候,我們不會這樣想的。我們會問:彩虹的顏色為甚麼這麼多?魚為甚麼會游泳?汽車為甚麼跑得這樣快?媽媽,為甚麼你愛我?
—那時我們不會畫地為牢,不會封鎖自己的好奇心。
寫作本書的時候,我覺得快樂。
這種快樂,就像19年前一樣—那是1997年12月的一個下午,我是個大學一年級生,當天早上,我剛完成「大學生涯」第一次期終試,真好!考試結束,可以跑圖書館了。到圖書館幹甚麼呢?我想知道一個「問題」的「答案」—
五代(907–960)時期事奉四朝、十帝的馮道(882–954),他對自己評價很高,自認「孝於家……『忠於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
馮道說:他自己「忠於國」—說這話的時候,他將近70歲,已經侍奉過三個朝代。
相反,北宋歐陽修(1007–1072)認為屢次「變節」的馮道,「可謂無廉恥者」。對於同一個人物,評價為何如此不同?馮道根據甚麼標準,在侍奉多朝以後仍然認為自己「忠於國」;歐陽修又根據甚麼準則,批評馮道「無恥」?
這不是哪個科目或哪一位老師給我的課業,只是我閒時閱讀想不通的事情—我想知道答案,更難以遏止自己的好奇心。於是,在1997年聖誕假期,我用了半月時間,寫了一篇只給幾個人看的文章,回答「如何評價馮道」的問題。我記得,當我用家中「噴墨式打印機」列印文稿,看着文章艱難地從打印機隙縫匍匐出來的時候,我很快樂。
後來我才知道,古今學者早就分析過這問題呢。而現在,我那篇「少作」都不知道跑哪裏去了。雖然如此,2007年我在香港城市大學講授「中國思想與文學」科目時,我還是偷偷把當年的念頭放在講義裏,專門以馮道和王安石(1021–1086)為例,分析「中國古代評價人物的標準」,以此作為自己學習旅途的紀念。我私下認為,這篇我已找不回的文章,是我「學術生命」的起點。或者說:當時的「快樂」,是我從此走上學術道路最大的理由。
讀書應該快樂,我們有時候居然會輕易忘記這一點。我想通過「通識科目」(城大稱為「精進教育Gateway Education」),讓同學和自己找回這種樂趣。
當然我們面對的問題是:有些人覺得「通識科目」與自己的「專業」無關—某某主修商業、生物、電子工程,為甚麼要他們認識「基督宗教與中國」?但小時候,我們不會這樣想的。我們會問:彩虹的顏色為甚麼這麼多?魚為甚麼會游泳?汽車為甚麼跑得這樣快?媽媽,為甚麼你愛我?
—那時我們不會畫地為牢,不會封鎖自己的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