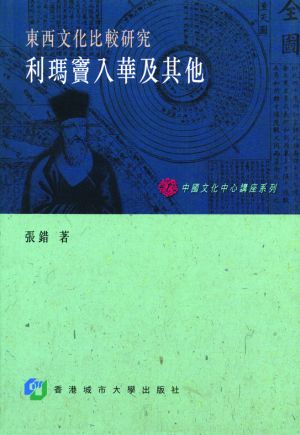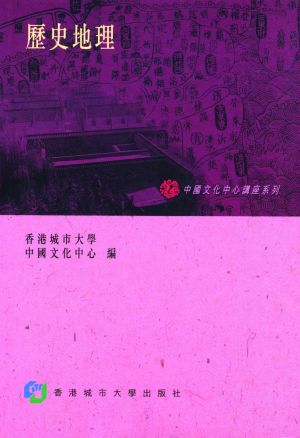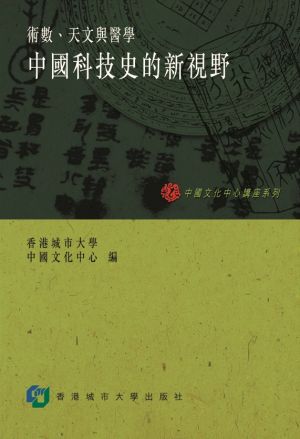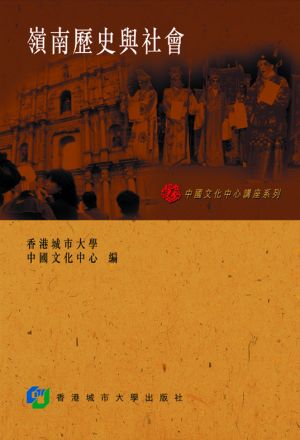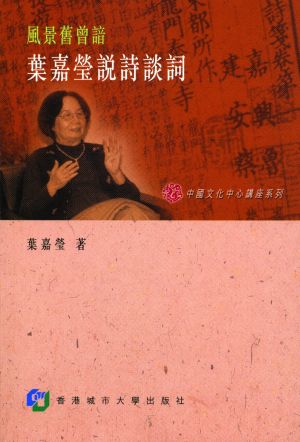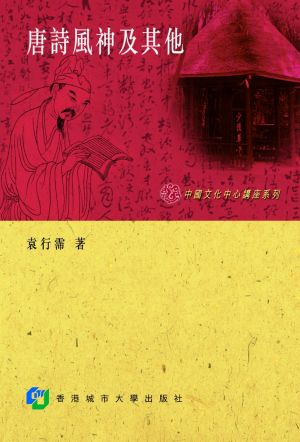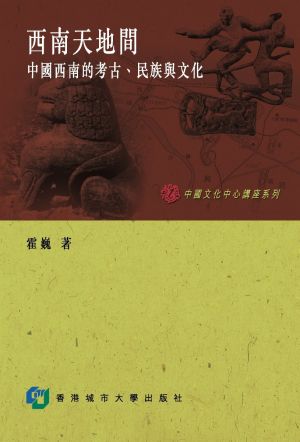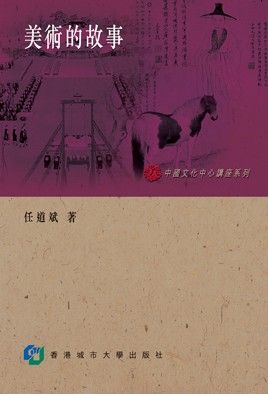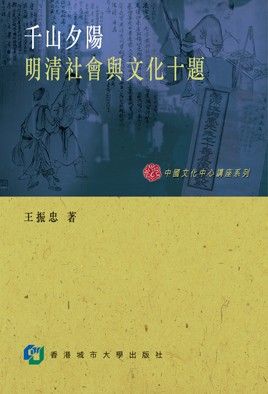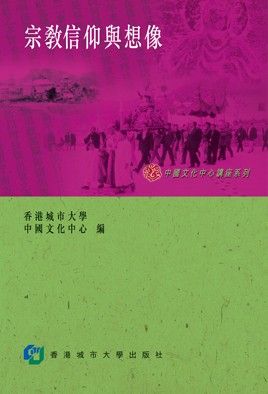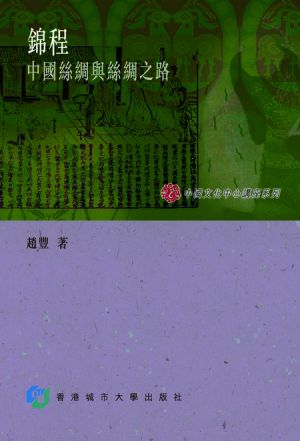中外文明交流是個大題目,也是人人都感興趣的題目。按照費正清的提法,中國近現代史就是一部中西文化接觸史,是西方挑戰、中國回應的歷史進程。這個說法,毋寧是誇大了西方文明在中國近代歷史文化發展上的主導地位,但卻直截了當,點出了中國近現代變化的主要脈絡,是與西方的拓展有關。
也許是因為近代西方強勢文化的影響,中國人都會感到學習西方、模仿西方是大勢所趨,是文明的走向,是不可逆轉的歷史必然。學習與模仿,或是不自覺的崇洋媚外,或是有意識的自強不息,總之,是看到了近代西方文明有其優秀高超、值得仿效之處。俗語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看到其他文明有高度發展的成就,而起模仿之念,而有嚮往之心,是人類的自然本性。然而,文明的發展也使人們對自己習慣的文化形態與行為,產生認同感、秩序感、甚至依賴感,出現文化的自我本位現象。不同文化的接觸,在不威脅認同感與秩序感的情況下,很容易相互交流與學習。一旦某方挾其船堅炮利,以征服的姿態出現,對應而來的便是抗拒與排斥,乃至於心理秩序的崩潰及重建秩序之前的混亂。
中國文明的發展,在世界歷史上有其地緣上得天獨厚之處,不但自我完足、自成體系,而且歷史悠久,連綿不斷,產生了根深葉茂、瓜瓞的文化認同感與秩序感。在與近代西方接觸與衝突之前,中國文明所塑造的文化模式強調的是秩序,是天人合一的整體穩定,是長幼尊卑各明其序的大一統帝國。與外界的交流限於物質的交換,以及不威脅政治社會體制的宗教思想及零星的天文地理知識。19 世紀以來,中西接觸的格局大變,也促成了中國近現代的變革與動盪。史學家形容近現代中國的歷史發展與走向,常用「尋求新秩序」這概念,其實就暗示了中國走出了舊的文明秩序,走進了全球化的世界格局,還沒找到穩定的新秩序,還在曠野大地上遊蕩。
中國古代知識界對外國的認識以及有系統的蒐羅材料,一向是實用性的,從張騫通西域到鄭和下西洋,都有天朝聲威遠播的政治目的。純知識的探討,為了了解域外文明而進行的研究很少,要到了20世紀才有系統而深入的專著。從馮承鈞翻譯的大量西方學術著作來看,早期的中西交通史研究領域,西方學者的貢獻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