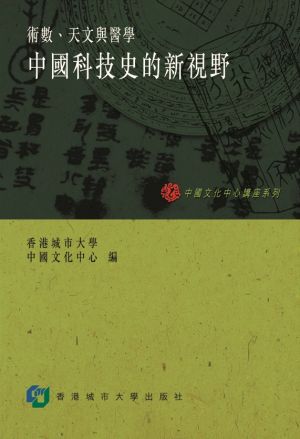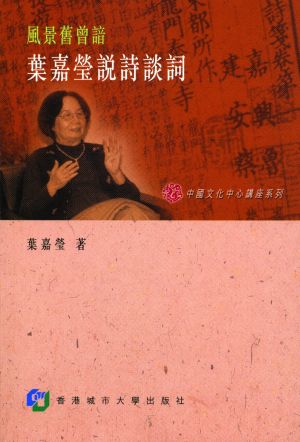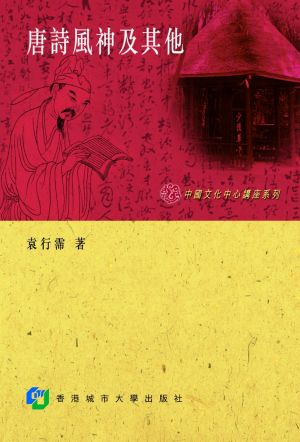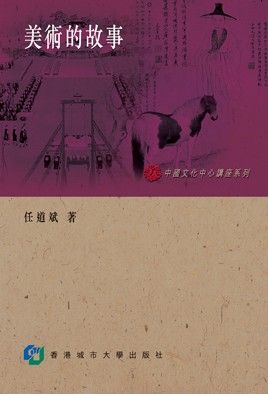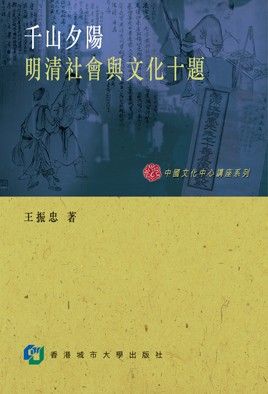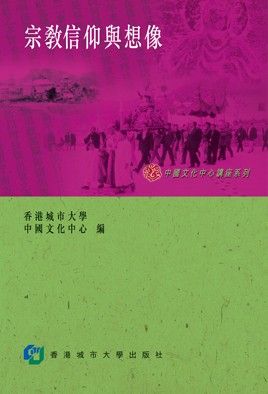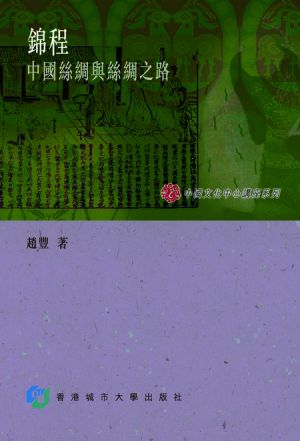《東西文化比較研究—利瑪竇入華及其他》一書,是我2001年秋季在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客座時,所做十個講座中的八講,多少代表了近年研究方向與努力。其實在總體十講裏,又可分為文化、藝術、與文學三大部分。本來讀比較文學出身的我,躋身於文學以外的比較文化及藝術,表面看來有點不務正業。但細觀之下卻並不盡然,因為比較文學發展到後來,停留在中西或東西方比來比去,已落下乘的聲聞辟支。反而在較大的文化文本裡,看出更深廣的涵面及意義。換句話說,我經常向自己詢問的問題,已經從「文學寫什麼?」轉變為「文學為什麼會這樣寫?」這種思潮改變,使我走出幾十年來純文學研究窠臼,而進入一個更大的文化宇宙。
也就是這種學術態度,使我對古代文物產生無限興趣與索求,即使不是主修藝術,但我可以從一面戰國或漢代銅鏡裡,看到蟠螭及虺紋圖騰無窮幻變,以及雲雷,波紋,鳥羽圖案背後的美學信仰。尤其是漢朝博局鏡,除了追尋好博漢人所奕的六博戲外,鏡內所顯示四靈與天人合一的和諧,以及求仙祈福或哀怨纏綿「長相思,毋相忘」的銘文,都令人閱讀古籍文字之餘,神往於古人圖象所表現的藝術境界。同樣是這種學術興趣,使一向對陶瓷極高興趣的我,花了五年多的時光,每晚上網學習閱讀拍賣行對陶瓷文物的描寫,從而昇堂入室,一探宋明名窯的奧秘。
除了閱讀瀏覽圖片與博物館的展出外,我沒有忘記在西安陜西歷史博物館內,第一次親眼看到祕色青窯那溫潤翠綠的狂喜。或是台北鴻禧美術館讓我親自手捧牙白劃花定碗,那種身歷其境的堅薄感覺,使我無怨無悔從書本堆中走出來。
除了閱讀瀏覽圖片與博物館的展出外,我沒有忘記在西安陜西歷史博物館內,第一次親眼看到祕色青窯那溫潤翠綠的狂喜。或是台北鴻禧美術館讓我親自手捧牙白劃花定碗,那種身歷其境的堅薄感覺,使我無怨無悔從書本堆中走出來。
利瑪竇滯華一共28年(1582-1610),但如從進入北京的 1600年1月24日開始算起,在京城活動只有九年。各項傳記及書信資料顯示,利氏居華廿餘載,自邊陲的澳門或肇慶,到中心的南昌或北京,無不顯現他的苦心孤詣,以折衷的西方教義溶入東方傳統,從而臻達宗教感化救世。利氏一生,象徵着這種努力的成功與挫敗。
如果我們分析這種努力,很快便會發覺,基督文明入華,有如一部《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尤其是耶穌會士的策略。從利瑪竇早期的「先僧後儒」到後期與佛教對決的「附儒佞釋」,解釋了這項歷程的求索努力(quest),除了竭力進入核心,敲開北京紫禁城大門,進謁萬曆帝外,還包括了以西方文明作為本位起點,進入中國版圖,學習並挑戰其文化為終點目標,臻達最後以宗教拯世教化目的。